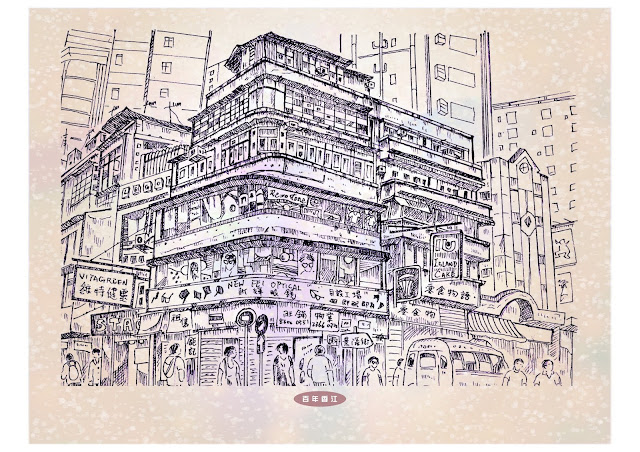「古法之佳者守之,垂絕者繼之,不佳者改之,未足者增之,西方畫之可採入者融之。」
------近代藝術大師 徐悲鴻
二十年代,中國剛經歷「五四新文化運動」,處於文化藝術革新的初期,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乃北大教授陳獨秀,起先他在其創辦之《新青年》雜誌中發表了《新文化運動是什麼》一文,其後更發表了關於《美術革命》的文章,認為要實現我國美術的改革,首要先革「四王」畫的命,「四王」即清代以來,以王時敏、王鑒、王石谷及王原祁為首的四位畫家所創立的院體山水畫派,該派的中心思想是「重視臨摹古人、反對創新。」
美術革命的後果,必然引起我國近代美術史上空前激烈的爭論及爭鬥,形成了「革新派」及「傳統派」,前者提出以西畫的方法及材料,用作改革國畫;後者則以捍衛國粹,復興國畫為己任。
「革新派」的藝術家總是富前瞻性,其實早於1912年,西方藝術教育的思潮,已由留歐回歸的藝術家率先帶回本國,藝術專科學校,也紛紛成立,由這批藝術家及學者主持,他們踴躍投身於美術教育行列中,並提出中國繪畫改良的芻議,當中包括有劉海粟、顏文樑、豐子愷、潘天壽及其後才遠赴法國學藝的徐悲鴻和林風眠。
留歐載譽歸來具影響力者,徐悲鴻與林風眠,直是分庭抗禮,兩人皆先後留法學藝,但藝術風格與觀念,卻南轅北徹:前者深受普呂東、德拉克洛瓦及林布蘭等寫實主義畫家的影響,認為畫家必須重新獲得描繪的能力,作品需捕捉真實,並主張以西方的技法與概念去改革中國畫。後者則熱衷於印象主義、表現主義、野獸派及立體主義等新思潮,追求色彩、線條及感官形象,作構成要素,以發揮我國藝術的抒情的優點。
徐悲鴻一生致力於中國畫的改良,雖則將西畫寫實的概念融入其中,但始終堅持以中國畫的工具材料和形式來從事創作,在筆墨的應用上,在論述上是否定多於肯定,實踐上卻是相反!他的筆墨表現了個人獨創的面貌,如他放棄使用線條的皴法,喜用闊筆的潑墨法,並將素描融入筆墨之中。
筆墨是我國繪畫的基本語言,即使致力改良中國畫的徐悲鴻,在融入西畫要素的同時,仍堅持使用筆墨:其一是他始終採用國畫的材料和工具:其二是他愛用傳統中的勾、染、潑墨等方法,以墨當色彩;其三他堅持畫與書、印相互結合,認定此屬國畫的重要形式。
我國藝術向來重視「筆情墨趣」,此乃中國畫的意境與情趣。徐悲鴻在筆墨的應用,主要放在勾勒法和沒骨法上,如他的人物畫,多用勾勒法,但強調以觀察寫實求真,配光影效果,也繼承了以形寫神的傳統。
在花鳥動物畫中,徐悲鴻少用渴筆與焦墨,愛用濕筆,墨色濃淡有致、溫潤渾融,極少枯澀,筆墨必與對象造型、質量感統一,作品中重視結構的準確性,不容筆墨的書寫性破壞,形成了結構緊、用筆鬆的效果。
把素描融入筆墨,是精於寫實造型的徐悲鴻對改良中國畫的貢獻。他把具科學性的寫實造型:包括光影、解剖、比例及透視等寫實造型技法,融入筆墨中,是帶有素描形式的筆墨,令筆墨服膺於物象輪廓與形質之中,彼此高度統一,讓筆墨發揮造型的作用。
與徐悲鴻同時代的藝術家,皆懷抱改良中國畫的理想,即若不以西方寫實主義為圭皋,但對筆墨的獨立意義,總是有意無意地淡化,這是回應時代與文化改革帶來的時代傾向,但改良會否造成傳統形式的失落與退化,直至今天,仍在爭論中!